| 弗朗茨·博厄斯 | |
|---|---|
 | |
| 出生 | 1858年7月9日 |
| 逝世 | 1942年12月21日 |
| 教育程度 | 德國基爾大學物理學博士(1881) |
| 職業 | 人類學家 |
| 配偶 | Marie Krackowizer Boas (1861-1929) |
| 兒女 | Helene Boas Yampolsky (1888-1963)
Ernst Philip Boas (1891-1955) Hedwig Boas (1893/94) Gertrud Boas (1897-1924) Henry Herbert Donaldson Boas (1899-1925) Marie Franziska Boas (1902-1987) |
| 父母 | Meier Boas (1823-1899), Sophie Meyer Boas (1828-1916) |
弗朗茨·博厄斯(德語: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2],是德國裔美國人類學家,歷史特殊論學派的代表人物,現代人類學的先驅之一,享有「美國人類學之父」的名號[3]。他也是語言學家,美國語言學研究的先驅。他開創了人類學的四大分支: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以及文化人類學。[4]如同許多當年的先驅者,他的學科訓練來自其他學科;他獲得物理學博士,並從事地理學的博士後研究。他將科學研究方法運用於人類文化與社會的研究,這個領域先前植基於圍繞著奇聞軼事的巨型理論論述[5]。
早年生活與教育
法蘭茲·鮑亞士生於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明登市。雖然他的祖父母是不折不扣的猶太人,其雙親卻如同大多數的德籍猶太人,依循著啟蒙時代的價值觀,其中包括同化於現代德國社會。鮑亞士對其猶太背景十分敏感,雖然他口頭上駁斥反猶太主義,並拒絕改信基督教,但他從不認同自己是猶太人;事實上,依據他的傳記作者所言:「他是一個『族群定義上』的德國人,在美國保存並提倡德國文化與價值」[6]。在一篇簡短自傳中,鮑亞士寫道:
我早年的思想背景來自一個德國家庭,其中1848年革命的理想是一股活躍動力。我的父親是自由主義者,但並不熱衷於公眾事務;我的母親是理想主義者,對公眾議題非常感興趣;他們在1854年於我的家鄉創立了幼稚園,致力於科學。我的父母砸碎了教條的枷鎖。我的父親對他父母親的家庭的禮儀,依然保持着一份情感,但並不允許這份情感影響他的知識自由。
鮑亞士從早年在明登市福祿貝爾幼稚園的經歷,到他在文理中學的學習中,接觸了博物學並對它產生了興趣。在他在「文理中學」的工作中,他最感興趣與自豪的是植物地理分布研究。然而,在鮑亞士進入大學就讀後,起先在海德堡大學,後來到波昂大學──他在波昂加入Burschenschaft Alemannia兄弟會,並終身參與它的活動──他關注的卻是數學和物理學(儘管他也選修一些地理學課程)。他當時有意前往柏林學習物理學,但為了更親近家人而選擇基爾大學。在那裡他向卡思登學習物理學。鮑亞士希望從事有關常態分布的高斯定理的研究,而卡思登卻引導他研究水的光學特性。該研究成為他博士論文的基礎。
1881年,鮑亞士在基爾大學獲頒物理學博士學位。他對他的論文並不滿意,反而對他從事研究期間深感困擾的感知問題,產生了興趣。當鮑亞士在海德堡修習庫諾·費雪的美學課程時,以及在波昂修習首屈一指的康德主義哲學家班諾·厄德曼(Benno Erdmann)的課程時,他已對康德學派思想產生興趣。這一興趣促使他轉向「精神物理學」,關注物理學之中的心理學和認識論問題的一門學問。他再度考慮前往柏林向赫爾曼·馮·亥姆霍茲學習精神物理學,但是精神物理學在當時的地位並不確定,而且鮑亞士並未受過心理學訓練。
畢業後的研究
巧合的是,提歐伯·費雪(Theobald Fischer)已移居到基爾,且鮑亞士已將地理學視為一條途徑,用以探索他對介於主觀經驗與客觀世界間的關係,所逐漸增長的興趣。在當時,德國地理學家們在討論文化變異的原因這個議題上,劃分為兩派。許多人主張,自然環境是主要決定因素;但其他人(特別是瑞特佐Friedrich Ratzel)試圖證明,思想透過人類遷移而傳播是更重要的。1883年鮑亞士前往巴芬島從事地理學研究,探討自然環境對於當地因紐特人遷移的影響。這是鮑亞士的許多民族誌田野工作的第一個,他摘錄田野筆記,撰寫他第一本專著:《中央愛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1888)。
鮑亞士與巴芬島的因紐特人共同生活並從事研究,而且他對於探討人們的生活方式,發展出終生的研究興趣。
鮑亞士記述,在北極圈冬季的永夜期間,他與旅行同伴迷路,被迫繼續駕著雪橇達26小時之久,穿越冰層、軟雪、以及降到零下四十六度的低溫。後來,他們安全到達一處遮蔽處休息,並從「飢寒交迫」中恢復過來。第二天,鮑亞士在他的信函日記中寫下:
我經常自問,我們的完善社會勝過於這些「野蠻人」的優點是什麼,而且發現,當我越是看到他們的風俗,越覺得我們沒有權利鄙視他們......。我們沒有權利因為他們的生活形式與迷信,在我們看來似乎相當可笑,而責怪他們。相對來說,我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糟糕...[7]。
鮑亞士在同一封信繼續解釋:「因此,個人可為人類提供的所有貢獻,必須用在提倡事實」。鮑亞士被迫依賴不同的因紐特群體來取得所需的一切,從方位與食物到遮蔽處與友誼。這是艱困的一年,充滿著許多極大的困難,包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疾病、不信任、黑死病與危險等等的襲擊。鮑亞士成功探索了許多未曾調查的區域,並發現獨特的民族誌事實,但漫長冬季與寂寞的越過危險地形的長途跋涉,迫使他探索他的靈魂,為他做為科學家與公民的生命,找尋一個方向。
鮑亞士對於原住民社群的興趣,在他任職於柏林皇家民族學博物館時逐漸增長。他在柏林經過介紹而結識加拿大卑詩省Nuxálk 民族的成員,這觸發他與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終生的關係。
他回到柏林以完成其研究,且在1886年(在亥姆霍茲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對其大學任教資格論文《巴芬陸地》(Baffin Land)進行答辯,並被任命為地理學「無薪大學教師」(privatdozent)。
當他在巴芬島時,他開始發展對於非西方文化研究的興趣。更進一步,1885年鮑亞士前往位於柏林的皇家民族學博物館,與體質人類學家魯道夫·菲爾紹和民族學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在兩年前(1883年),鮑亞士為了準備前往巴芬島探險,曾向菲爾紹學習解剖學。當時,菲爾紹捲入一場與他昔日學生恩斯特·海克爾之間對於演化的喧囂爭論。海克爾在閱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決定放棄他的醫生職業,改而研究比較解剖學,而且不遺餘力地在德國推廣達爾文思想。然而,如同其他大多數在1900年重新發現孟德爾遺傳學以及1918年現代綜合理論發展之前的自然科學家,菲爾紹感覺達爾文的理論是薄弱的,因為他們缺乏一套細胞突變性的理論。因此,菲爾紹偏愛拉馬克學派的演化模型。這一爭論在地理學家中引起共鳴。拉馬克論者相信環境力量可以促成有機體快速與持久的變化,該變化並沒有遺傳原因;因此拉馬克論者和環境決定論者時常發現他們處在爭論的同一方。
而鮑亞士與巴斯典更為密集地工作,後者以其對環境決定論的反感而著名。取而代之的,他試圖證明「人類心智一致性」,這是一個信念,所有的人類都具有相同的知識能力,以及所有文化都基於相同的基本心智法則。他試圖證明,習慣與信仰的變異是歷史偶然事件的結果。這一觀點呼應鮑亞士在巴芬島的經歷,並吸引他轉向人類學。
在皇家民族學博物館時,鮑亞士開始對太平洋西北海岸的美洲土著產生興趣,並且在他對大學任教資格論文進行答辯後,他經由美國紐約前往加拿大卑詩省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紐約獲得《科學》(Science)雜誌的助理編輯一職。鮑亞士遠離了在德國愈演愈烈的反猶太主義與國家主義,以及對地理學家而言極其有限的學術機會,他決定留在美國。
除了他在《科學》雜誌的編輯工作,鮑亞士在1888年還獲得了美國克拉克大學人類學講師「dozent」的職位。但鮑亞士在克拉克大學的機會有限,因為這所大學並未設立人類學系。而且,鮑亞士擔心大學校長斯坦利·霍爾對其研究的干涉。1892年,鮑亞士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學教師的辭職行列,以抗議霍爾對學術自由的侵犯。鮑亞士此後於1893年被任命為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人類學首席助理。
十九世紀末論辯
科學對立於歷史
有某些學者,如鮑亞士的學生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認為鮑亞士運用其物理學研究模式,做為進行人類學研究的方針。但其他許多人,如鮑亞士的學生亞歷山大·萊瑟(Alexander Lesser),以及後來的研究者如瑪麗安·史密斯(Marian W. Smith),赫伯特·劉易斯(Herbert S. Lewis)和馬蒂·班佐(Matti Bunzl),指出鮑亞士明確拒絕物理學,而是支持以歷史學作為他的人類學研究模式。
此種科學與歷史間的差別源自於19世紀的德國學術界,他們區分Naturwissenschaften(科學)與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學),或區分Gesetzwissenschaften(提出定律的科學)與Geschichteswissenschaften(歷史學)。一般而言,在這兩組術語之中,前者指涉對於受客觀自然法則支配之現象的研究,後者指涉那些只有從人類感知或經驗的角度來看,才會具有意義的現象。在1884年,康德哲學學派哲學家威廉·文德爾班創造了律則式(nomothetic)和個殊式(idiographic)這兩個名詞,以描述這兩個方向殊異的方法。他觀察到多數科學家混合使用此兩種方法,但比例各不相同;他將物理學視為律則式解釋的絕佳範例,而歷史學則是個殊式解釋學科。而且,他主張這兩者每個都源自於康德對於理性的兩種「興趣」之一,這是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到的──其一為「歸納」(generalizing),其二為「詳細說明」(specifying)。(文德爾班的學生海因里希·李凱爾特在〈自然科學概念形成的限制:對歷史科學的邏輯性介紹〉一文中,闡述了這個差別;鮑亞士的學生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和愛德華·薩丕爾大量依賴這篇文章來界定他們的人類學方法。)
儘管康德認為對理性的這兩種興趣是客觀與普遍的,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區別已在德國被制度化,這是透過在啟蒙運動之後的學術研究與教學組織。在德國,啟蒙運動由康德本人所主導,他試圖建立一些植基於普遍理性的法則。在對康德的回應中,德國學者如赫爾德主張人類的創造力,它必然採取不可預測與高度變異的形式,而且與人類理性同樣重要。1795年,偉大的探險家與博物學家威廉·馮·洪堡呼籲建立一套人類學,結合康德與赫德的興趣。洪堡於1809年創立柏林大學,他的地理學、歷史學與心理學著作,也提供鮑亞士賴以使其知識傾向趨於成熟的環境。
在洪堡學派傳統下從事研究的歷史學家,發展了一些概念,成為鮑亞士學派人類學的核心思想。蘭克將歷史學家的任務界定為「全然如實呈現歷史確實的樣貌」,這是鮑亞士經驗論的基石。威廉·狄爾泰強調了「理解」在人類知識的中心地位,並強調一個歷史學家的經歷可提供一個基礎,用於對一位歷史行動者的處境,產生一種感同身受的理解。對鮑亞士而言,兩者的價值可引述歌德的話而完美表達:「一個個別行動或事件是令人感到有興趣的,這不是因為它是可解釋的,而是因為它是真實的。」
這些思想對鮑亞士的影響,顯現於他1887年的短文〈地理學研究〉("The Study of Geography"),其中他區別了自然科學(試圖探索決定現象的某些法則)與歷史科學(尋求從現象自身的角度,對現象產生一個徹底理解)。鮑亞士主張,就這個意義來說,地理學確實是而且必須是歷史的。1887年,在他的巴芬島探險之後,鮑亞士寫下了《民族學分類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Ethnological Classification"),在文中他發展了這一論點,運用於人類學:
民族學現象是人類的體質與心靈特質的產物,也是這個特質在周遭環境影響下發展的產物……「環境」是國家的外在條件,也是社會學現象,換言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且,對現有環境的研究是不夠充分的:人群的歷史,透過人群的遷移而傳遞的這些區域的影響力,以及他們所接觸的人群,都必須納入考慮。
這個陳述呼應了瑞特佐對於人類遷移和文化接觸的歷史過程的關注,以及巴斯典對環境決定論的拒斥。它也強調了文化如同一個脈絡(context)(「環境 (surroundings)」),以及歷史的重要性。這些是鮑亞士學派人類學(馬文·哈里斯後來稱之為「歷史特殊論」)的註冊商標。引導了鮑亞士往後十年的研究,以及他對往後學生的指導。(參閱[Lewis 2001b]有別於哈里斯的觀點。)
雖然脈絡和歷史是鮑亞士將人類學理解為「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學)和「Geschichtswissenschaften」(歷史學)的基本要素,鮑亞士學派人類學仍與「Naturwissenschaften」(科學)具有一個共同的基本要素:經驗論。在1949年,鮑亞士的學生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總結了一些經驗論法則,這將鮑亞士學派人類學界定為一門科學:
- 科學方法是始於問題,而不是始於答案,至少對所有的價值判斷而言。
- 科學是不帶感情的研究,也因此不能完全取代任何一種「已在日常生活中明確表述的」意識型態,因為這些意識形態本身不免在傳統上或規範上,帶有情緒成見的色彩。
- 徹底的全有或全無、黑與白的判斷方式是極權主義態度的特徵,而且在科學之中不具任何地位,科學的本質是推論與公正的。
直生論對立於達爾文演化論
鮑亞士及其學生的最偉大成就之一,是他們對當時的體制、社會與文化的演化理論潮流的批判。這一批判是鮑亞士在博物館工作和他在人類學四大分支工作的核心。
基於這項理由,某些人主張鮑亞士派人類學與達爾文的演化論相衝突。這個論點是沒有根據的,且錯誤地設想人們經常使用「演化」一詞來指稱同一事物。實際上,鮑亞士支持達爾文的理論,儘管他並不認為它可以自然而然地適用於文化和歷史現象[8]。鮑亞士學派所嘲笑與拒斥的是當時盛行的直生論。直生論是一個確定的或目的論的演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變異是向前推進的,而與自然選擇無關。鮑亞士拒斥這套由愛德華·伯內特·泰勒、路易斯·亨利·摩爾根以及赫伯特·斯賓塞所發展的盛極一時的社會文化進化論,並不是因為他反對「演化」概念本身,而是他贊同達爾文的演化觀而反對直生論的演化觀。
這些盛行的文化演化理論與達爾文的理論之間的差異不能被誇大:這些理論家主張,所有社會的進步都歷經以一套相同次序中的幾個相同階段。因此,儘管鮑亞士在巴芬島所研究的因紐特人,與他在擔任大學研究生時所研究的德國人,兩者是同時代的,但演化論者主張因紐特人處於他們演化的早期階段,而德國人在晚期階段。這呼應著一個流行的對達爾文的誤讀,人類是源自於黑猩猩。實際上,達爾文主張黑猩猩和人類同樣是演化而來的。足以描寫達爾文理論的特性的是,它關注某個物種轉變成另一個物種的「過程」;「適應」是解釋某一物種及其環境間關係的關鍵法則;以及「自然選擇」作為一個轉變機制。相對地,摩爾根、斯賓塞與泰勒極少提及轉變的過程和機制。
除此以外,達爾文透過對大量經驗資料的謹慎檢視而建立其理論。鮑亞士學派研究顯示,事實上文化演化論者的每個主張都與資料相矛盾,或反映了對資料的深刻誤解。正如鮑亞士的學生羅伯特·羅維所評述的:「與某些關於這項主題令人誤解的陳述相反的是,並沒有任何可信賴的反對演化觀念的論點,是經過科學方法證實的,儘管仍有一些對於演化形而上學的堅強敵意,扭曲了確立的事實。」
在一份未出版的講稿中,鮑亞士描述了他歸功於達爾文之處:
儘管這個思想並未十分明確表現達爾文對精神力量發展的討論,看來相當清楚的是,他的主要目標是表達他的堅定信念,各種心智能力的發展並不具有一個確切的目的,而是它們源自於變異,而且透過自然選擇而被延續。這一思想亦由華萊士明確表達,他強調某些外表看似合乎理性的人類活動,可能是在並未確實運用理性思考的情況下,而完善地發展出來。
因此鮑亞士暗指的是,表面上看似一個文化之中的各種模式或結構,並不是有意識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不同機制(例如傳播與獨立發明)所產生的結果,它們產生了由人們生存與行動於其中的社會環境所塑造的文化變異。鮑亞士藉由確認達爾文著作的重要性,總結他的這篇講稿:
我希望我已成功呈獻給各位——儘管仍有缺陷——歸功於不朽的達爾文作品所引發的這些思潮,已造就了人類學的今日樣貌。(Boas, 1909 lecture; 見Lewis 2001b.)
學術生涯早期:博物館研究
在19世紀晚期,美國人類學受到美國民族學局的控制,由約翰·威斯利·鮑威爾擔任局長,他是一位地質學家,支持摩爾根的社會文化進化論。美國民族學局座落於華盛頓的史密森學會,且史密森的民族學主管歐提斯·梅森與鮑威爾一樣信奉文化演化(哈佛大學的皮博迪博物館(Peabody Museum)是個重要的——儘管規模較小——人類學的研究中心)。
正是在鮑亞士為博物館徵集藏品與展覽而工作期間,鮑亞士形成了其對文化的基本見解,這使他離開博物館,而尋求將人類學建立為一門學科。
在這段期間,鮑亞士再度前往太平洋西北岸,達五次之多。他持續進行的田野研究使他想到,文化做為解釋人類行為的一個地方脈絡。他對於地方脈絡和歷史的強調,使他反對當時的主流思想模式:社會文化進化論。
鮑亞士起初在親屬關係問題上,與演化論相決裂。摩爾根主張,所有人類社會都是從最初的母系組織形態轉變為父系組織。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北海岸的印第安團體,如欽西安人(Tsimshian)和特林吉特人,都是被歸類到母系氏族。而南海岸的印第安人如努特卡人(Nootka)以及薩利什人(Salish)被歸類為父系團體。鮑亞士關注夸扣特爾人,他們居住在上述兩群之間。夸扣特爾人似乎具有混合特徵。在婚前,一個男人將採用其妻子父親的名字和羽飾。他的孩子也採用這些名字和羽飾,儘管他的兒子在結婚時就會失去它們。名字和羽飾因此保存在母系中。起初,鮑亞士如在他之前的摩爾根一樣,認為夸扣特爾人曾經和他們北方鄰族一樣是母系的,但後來他們開始演化到父系團體。然而1897年他進行了自我批判,並且主張夸扣特爾人是從早先的父系組織轉變成母系組織,這是由於他們向北方鄰族學習了母系原則。
鮑亞士對摩爾根理論的拒斥,導致他在一篇於1907年發表的文章裡,挑戰歐提斯的博物館展示原則。然而,更有問題的是關於因果關係及分類的基本問題。物質文化的演化觀點使得博物館研究人員根據技術發展的功能或級別來組織展品。研究人員假定器物的形態變遷,反映了一些前進式演化的自然過程。但鮑亞士認為,一件器物的形態反映了其被製作和使用的環境。鮑亞士主張「儘管類似的原因產生類似的結果,但類似的結果不見得具有類似的原因」。鮑亞士認識到,即使是形態相似的器物,也可能基於不同原因,而在不同脈絡中發展出來。歐提斯的博物館展示依據幾條演化路線來組織,錯誤地將類似結果並置在一起;那些沿著脈絡路線而組織的展示,將會呈現類似的原因。
1892年,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館長暨研究員普特曼被任命擔任芝加哥博覽會民族學與考古學部門的負責人,鮑亞士獲聘擔任他的助理,鮑亞士因此有機會將他的研究取向運用於展示。鮑亞士安排了十四位來自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夸扣特爾人來到芝加哥,並居住在一個仿造的夸扣特爾人村落中,他們可在那裡依據脈絡來進行其日常工作。
在世界美洲博覽會之後,鮑亞士在芝加哥新設立的費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工作直到1894年,當時他的職位(在違反他的意志下)由美國民族學局的考古學家霍姆斯所接替。1896年,鮑亞士被任命為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擔任民族學與人體學的助理研究人員。1897年他組成了傑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隊(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一場為期五年對於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這些人的祖先是從西伯利亞跨越白令海峽遷移而來。他嘗試沿著脈絡的路線來組織展示,而不是沿著演化路線。他也發展了切合其策展目標的研究計畫:從擴大在一個社會之內的各種詮釋脈絡的這個角度,來描述他對學生所下的指令,他解釋說:「...他們自己取得標本;他們取得對這些標本的解釋;他們取得相關文字資料,一部分關聯到這些標本,一部分關聯到這個人群的概況;而且他們取得當地語言的語法資料」。這些擴大的詮釋脈絡全被抽離進入一個脈絡,這是這些標本或標本組合體,可能被展示的脈絡:「我們希望有一套蒐藏品,依據各個部族來安排,這是為了傳達每個群體的特殊風格」。然而,他的取向使他與博物館總裁傑瑟普(Morris Jesup)以及館長班普斯(Hermon Bumpus)發生衝突。他於1905年辭職,再也沒有為任何博物館工作。
學術生涯晚期:學院人類學
1896年,鮑亞士被任命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體質人類學講師,並於1899年升等為人類學教授。然而,在哥大教學的人類學家分屬不同科系。當鮑亞士離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他與哥倫比亞大學協商將人類學家集中到同一個系,鮑亞士將主持該系。鮑亞士在哥大的人類學系成為美國第一個設立博士課程的人類學系。
在這段期間,鮑亞士發揮了關鍵作用,將美國人類學會組織這個新興領域的一個傘形結構組織。鮑亞士起初希望美國人類學會的成員限定為專業人類學家,但是麥克基(W.J. McGee)(另一位參與由鮑威爾所領導的美國民族學局的地質學家)主張,該組織應當開放其他學科加入成員。麥克基的立場站了上風,而且他在1902年被選為美國人類學會的首任主席。鮑亞士與普特曼(Putnam)、鮑威爾和荷曼斯(Holmes)同時被選為副主席。
鮑亞士同時在哥大和美國人類學會,鼓吹人類學「四大分支」的概念;他親自為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以及文化人類學做出貢獻。他在這些分支的工作擔任開路先鋒:在體質人類學,他領導學者遠離種族的靜態分類學,而強調依照人類生物學與演化進行分類;在語言學,他打破了經典文獻學的侷限,並確立一些現代語言學及認知人類學的核心問題;在文化人類學,他(與馬凌諾斯基一起)建立了脈絡論者的研究取向,探討文化、文化相對論與田野工作的參與觀察法。
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被認定不僅將不同類型的人類學家集中到一個科系,更是透過將人類學研究的不同課題整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課題,來重新設想人類學,這是鮑亞士對這個學科的重大貢獻,並成為美國人類學有別於英國、法國、德國等國人類學的特徵。這個研究取向將人類學的課題──人類物種界定為一個整體。這個焦點並未使鮑亞士尋求將所有的人類與人類活動形態化約為某些最小公分母;更恰當的說,他明白人類物種的本質,將是在於人類形態與活動方面的為數龐大的變異(這是一條類似於達爾文探討一般物種的研究取向)。
在他1907年的文章〈人類學〉中,鮑亞士為人類學家確定兩個基本問題:「為什麼世界上的部落和民族會有所差異?現在的差異是如何發展出來的?」由這些問題推而廣之,他解釋了人類學研究的目標如下:
我們並不是討論一個個體的人類所具有的解剖學的、生理學的與心智的特質;我們感興趣的卻是,這些特徵在不同地理區域與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類群體中的多樣性。我們的任務就是探究引發這些被觀察到的差異的原因,並調查引致人類生活多樣形態的建立的一些事件的發生順序。換言之,我們感興趣的是,生活在相同生物、地理與社會的環境下的人們,所具有的解剖學的與心智的特質,而且將其視為由它們的過去所決定的。
這些問題標示着一個與當時流行的人類多樣性思想的明顯決裂,後者假定某些人群具有歷史,明顯記載於歷史(或書寫)記錄中,然而其他人群欠缺文字記錄,也就欠缺歷史。對某些人而言,介於兩種不同類型社會間的這項區別,解釋了介於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及其他關注文字記錄的學科,與人類學這個被假定專注於無文字記錄的人群的學科之間的差異。鮑亞士拒斥這種介於兩種社會類型間的區別,以及這套學術分工。他了解所有的社會都具有歷史,且所有社會都可成為人類學研究的合適對象。為了以相同研究取向探究有文字與無文字社會,他強調透過對文本以外事物的分析,研究人類歷史的重要性。因此,在他1904年的文章〈人類學的歷史〉("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鮑亞士寫道:
人類學家作品的歷史發展,似乎清楚地挑選一個迄今尚未由其他任何科學所涉足的知識領域。這就是所有不同人種的生物史;運用於無文字語言人群的語言學;對於無歷史記錄的人群的民族學;以及史前考古學。
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及社會理論家已在思索關於這些差異的起因,但鮑亞士拋棄了這些理論,特別是占主流地位的社會文化進化論。他努力建立一門學科,這門學科的主張將會植基於嚴格的經驗研究。
他在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原始人的思維》(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1911年出版)——整合了上述各種關注,並建立了一個人類學系,主導了美國人類學往後十五年的發展。在這項研究中,他確立了任何特定人群、生物學、語言、物質的與象徵的文化均為自主的;每一個都是同等重要的人類行為面向,但其中沒有任何一個面向可以化約為另一個。換言之,他確立了文化並不是任何獨立變項的依變項。他強調任何人群的生物、語言與文化特徵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其中包含了文化與非文化力量。他確立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一個基本特徵,而且這個特定文化環境建構了許多個體行為。
鮑亞士也將自己呈現為一個公民科學家的角色模範,他理解即使有對於真相的追求做為他的目標,所有知識都具有道德結果。《原始人的思維》一書以對人文主義的呼喚做結:
我希望在書中略述的這些討論已經呈現,人類學資料教導我們,對有別於我們的文明類型抱持更大寬容,我們應學着以更大同理心來看待異己種族,並抱持一種堅信,當所有種族都以某種方式,對以往的文化進展做出貢獻,因此他們也將能促進人類的利益,只要我們願意提供他們一個公平機會。
體質人類學
鮑亞士的體質人類學研究,結合了他對達爾文演化論以及將遷移視為變遷原因的這兩個研究興趣。他在這個領域的最重要作品是對紐約移民子女體型改變的研究。其他研究者已提出在美國人與來自歐洲不同地區的人們間,身高、頭骨尺寸、以及其他體質特徵的差異。許多人運用這些差異,主張不同種族間存在著先天的生物差異。鮑亞士的主要興趣是對於變遷過程研究──針對象徵文化、物質文化及語言;他因此開始測定是否體型也受變遷過程所影響。鮑亞士研究了17,821個人,區分為七個民族─國家群體。鮑亞士發現移民的頭骨尺寸平均值,明顯有別於在這些分組之中出生於美國的成員。此外,他發現由母親在抵達美國之後的頭十年內所生的孩子,其頭骨尺寸的平均值,明顯有別於那些在母親抵達十年之後所生的孩子。鮑亞士並不否認體質特徵是遺傳的,例如身高或頭骨大小;然而,他確實主張環境對這些特徵具有影響力,這是隨時間變化而被顯現出來。這項工作對於他深具影響力的主張——種族間的差異並非不可改變的——具有核心地位。
在當時,這些發現是激進的且依然持續爭論中。2002年人類學家史巴克斯(Corey S. Sparks)和詹茨(Richard L. Jantz)宣稱,由相同父母在歐洲和美國所生的孩子之間的差異極小且不顯著,而且暴露於美國環境中,對孩子的頭骨指數並未發生可察覺的影響。他們主張其研究結果與鮑亞士原先的發現相矛盾,並論證鮑亞士的發現可能不會再被用來支持頭骨形態學中的可塑性論點[9]。然麥克斯(Jonathan Marks)——著名的體質人類學家以及美國人類學會前任的普通人類學部門主席——指出這項對鮑亞士工作的修正研究「具有絕望(如果不是困惑)論調,而且很快受到更多主流生物人類學所反駁[10]。 在一份稍後的出版品,Gravlee、Bernard和Leonard重新檢視史巴克斯和詹茨的分析。他們主張史巴克斯和詹茨扭曲了鮑亞士的論點,而史巴克斯和詹茨的資料確實支持鮑亞士。例如他們指出,史巴克斯和詹茨檢視頭骨尺寸的變化,將它關聯到個體在美國居住的時間長度,以測試環境的影響。然而,鮑亞士檢視頭骨尺寸的變化,將它關聯到個體的母親在美國居住的時間長度。他們主張鮑亞士的方法更為有效,因為出生前環境是一項重要的個體發展因素[11]。
儘管一些社會學家和演化心理學家指出,鮑亞士反對達爾文演化論,但鮑亞士實際上是達爾文演化思想的忠實支持者。在1888年,他宣稱「民族學的發展大部分歸功於對生物演化原則的普遍認定」;從鮑亞士的時代以來,體質人類學家已確立,人類的文化能力是人類演化的產物。實際上,鮑亞士的體型變化研究對於達爾文學說的興起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要的是請記得,鮑亞士是在生物學家對於遺傳學毫無所悉的時代被訓練出來的學者;孟德爾遺傳學直至1900年後才廣為人知。先前的生物學家依賴對體質特徵的測量,作為支持任何演化學說的經驗數據。然而,鮑亞士的生物測量研究,使他質疑該方法與資料類型的效用。1912年,在柏林對人類學家發表的一場演講中,鮑亞士主張這種統計學方法挺多只是增加生物學的問題,而無法解答它們。正是在這種脈絡下,人類學家開始轉而以遺傳學作為任何理解生物變異的基礎。
語言學
儘管鮑亞士曾出版對美國土著語言的描述研究,並撰寫關於語言分類工作在理論上的困難之處,他仍將這個主題留給同事與學生如薩丕爾去研究文化與語言間的關係。
但是,他1889年的文章《關於交替語音》("On Alternating Sounds")為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兩科的方法論,提供了非凡貢獻。這是對1888年丹尼爾·加里森·布林頓所發表論文的回應,當時布林頓為賓州大學的美國語言學與考古學教授。布林頓觀察到,在許多美國土著的口語中,某些語音規律地交替。這顯然不是個人口音所產生的作用;布林頓並未暗示說某些個體對於某些單字的發音異於他人。他主張有許多單字,甚至在被同一個說話者重複說出時,其發聲法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運用演化理論,布林頓主張此種普遍的不一致性是語言處於劣等的標記,以及美國土著都處於他們演化過程低等階段的證據。
鮑亞士對布林頓所討論的內容十分熟悉;他在巴芬島和太平洋西北從事研究時也經歷類似事情。然而,他主張「交替語音」絕對不是美國土著語言的特徵——甚至他主張它們根本不存在。鮑亞士並未將交替語音當做文化演化不同階段的客觀證據,而是從他多年來關於客觀自然現象的主觀感知的研究興趣,來看待它們。他也思考先前對演化取向的博物館展示的批評。在那裡,他指出兩種東西(如物質文化的器物)表面上看來是相似的,可能在實際上卻是非常不同。在這篇文章,他提出一種可能性,兩種東西(語音)看似不同,可能在實際上卻是相同的。
簡言之,他將注意力轉移到對不同語音的「感知」上。鮑亞士以提出一個經驗問題開始:當人們用不同方法描述一個語音時,是因為他們不能感知其差異,或是可能存在另一個理由?他立刻就確定立場,他不關心關於感知缺陷的個案——等同於色盲的聽覺障礙。他指出,這些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個語音的人們所具有的問題,等同於用相同方式描述不同語音的人們所具有的問題。這是研究描寫語言學的關鍵:當研究一種新語言時,我們如何注意不同單字的發音?(在這一點上,鮑亞士預見了並奠定了音位學(Phonemics)與語音學(Phonetics)的區別。)人們可能用多種方法來發音一個單字,而且依然認知他們正在使用同一個單字。那麼,問題並不是「這些知覺未能被他們個人所認知」(換言之,人們認知到某些發音的差異);而是這些語音「是依據其相似性而被分類」(換言之,人們將多種被感知到的語音歸成同一類)。一個類似的視覺例子包括描寫顏色的單字。英語單字「green」能被用來指稱多種明暗、色調、濃淡。但有些語言並沒有指稱「green」的單字。在這些案例中,人們可能將英語使用者所稱的「green」歸入「yellow」或「blue」中。這不是一個色盲的例子——人們能夠感知顏色的差異,但他們歸類這些相似顏色的方式有別於英語使用者。
鮑亞士將這些原則運用於對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因紐特語的研究。研究者們已發表某個特定單字的許多不同拼法。在過去,研究者透過許多方法解釋這項資料──它可能指出對某個單字發音方式的各地變異,也可能指的是不同方言。鮑亞士主張另一種解釋:差異並非在於因紐特人如何發出這個單字的語音,而是在於使用英語的學者如何感知這個單字的發音。這項差異並非在於英語使用者本身無法感知這個被討論的發音;而是英語的語音系統無法適應被感知的語音。
儘管鮑亞士對描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特殊的貢獻,但是他最終的論點是意義深遠:觀察者的偏見並不必然是個人的偏見,它可能是文化的。換言之,西方研究者的感知範疇,可能有系統地導致一位西方人誤解或無法完整感知另一文化中的一個有意義的成分。如同他對梅森的博物館展示所提出的批評,鮑亞士論證了這個看似文化演化證據的東西,實際上是不合乎科學的方法與西方人對自身文化優越的信念所產生的結果。這個論點為鮑亞士的文化相對論提供了方法論基礎:某個文化的各種成分,從該文化的角度來看是有意義的,即使它們從另一文化的角度來看是沒有意義的(或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文化人類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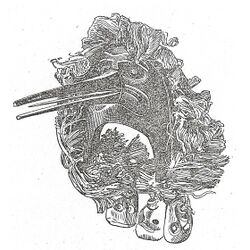
鮑亞士民族誌研究方法的本質,是立基於他早期對「地理學研究」的論文。在那篇論文,他支持一種研究方法,即
將每種現象都看成,因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值得研究的。它存在的這項事實,就使它足以獲得我們全心的注意;而且對於它在時空中的存在與演化的知識,完全滿足了求知者。
當鮑亞士的學生露絲·潘乃德在1947年向美國人類學會發表主席就職演說時,曾引用文學批評家布瑞迪(A.C. Bradley)的話:「我們注意的是『什麼是』,注視著它如何發生與勢必發生,」以提醒人類學家此種個殊式解釋(idiographic)立場的重要性。
這個取嚮導致鮑亞士提倡文化人類學,它的特色在於堅強致力於:
- 經驗論(對於以「科學定律」描述文化的各項嘗試,抱持著懷疑態度)
- 將文化視為流動與動態的觀念
- 民族誌田野工作,人類學家在被研究的人群中長期居住,以當地語言從事研究,並與當地研究者共同合作,作為蒐集資料的方法。
- 以文化相對論作為從事田野工作的方法論工具,以及在分析資料時具有啟發性的工具。
鮑亞士主張,為了理解「什麼是」——在文化人類學,特定的文化特質(行為、信仰和符號)——學者必須在它們的當地脈絡中檢視它們。他也了解到,當人們從某地遷到另一地,以及當文化脈絡隨時間而改變,一個文化的各種要素及它們的意義將會隨之改變,這導致他強調對於文化分析而言,當地歷史所具有的重要性。
儘管當時其他人類學家,如馬凌諾斯基以及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關注對各社會的研究,他們認為社會是有明確界線的,但鮑亞士將注意力放在歷史上,後者顯示了某些文化特質從某地傳播到另一地的程度,這致使他將文化界線視為多重與重疊的,並且是具有高度滲透性的。因此,鮑亞士的學生羅伯特·羅維一度將文化描述為一件「碎片和補丁」。鮑亞士和他的學生認為,由於人們試圖理解他們的世界,因此他們尋求將世界的完全不同的要素整合起來,結果是不同文化可能是以具有不同形貌或模式為其特徵。但鮑亞士學派也認為,這種整合狀態往往與傳播處於緊張狀態,而且任何一個穩定結構的表象都是暫時的(見Bashkow 2004: 445)。
在鮑亞士的一生中,正如同現在的情況,許多西方人看到介於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基本差異,前者是以物力論(dynamism)與個人主義為其特徵,後者則是穩定與同質的。然而,鮑亞士的經驗田野研究使他反對前述的對比。比如,他1903年的文章〈阿拉斯加人針箱的裝飾圖案:傳統設計的歷史,以一個美國博物館的材料為基礎〉("Decorative Designs of Alaskan Needlecases: A History of Conventional Designs, Based on Materials in a U.S. Museum" )提供了另一個例子,關於鮑亞士如何根據對經驗資料的細緻分析,而提出廣闊的理論主張。在確立了這些針箱的相似性後,鮑亞士呈現某些外形特質如何提供一套語彙,使個別工匠可從中創造設計變化。因此,他強調將文化視為一個脈絡,據以解釋有意義的行動,這使他對於一個社會中的個體差異感到敏感(威廉·亨利·霍爾姆斯在1886年的〈陶瓷藝術的外形與裝飾起源及其發展〉一文提出了類似觀點,儘管他不同於鮑亞士,他並未發展民族誌與理論的意涵)。
在1920年的一篇提綱挈領的文章《民族學的方法》(The Methods of Ethnology)中,鮑亞士主張,人類學需要的並不是「系統化列舉一個部族的經過標準化的信仰和習慣」,而是需要證明「個體的反應方式,包括對於他的整體社會環境,以及對於不同意見與行為模式,這些發生在原始社會中,而且是一些具有深遠影響的變遷的發生原因」。 鮑亞士主張,對個體能動性的關注呈現了「個體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社會環境所決定,但接下來他自己的活動影響了他生活其中的這個社會,且可能引發形態的修正」。因此,鮑亞士認為文化基本上是動態的:「這些方法一旦被採用,原始社會就失去了這個外表上的絕對穩定性……更正確地說,所有文化形態都呈現一種流動狀態……」(見Lewis 2001b)
在鮑亞士對於將有文字與無文字社會間的這項區別,作為一種界定人類學研究對象的方式的適當性,提出反對之後,鮑亞士主張無文字與有文字社會應當以相同方式被分析。十久世紀歷史學家已採用文獻學(philology)研究技術,重建有文字社會的歷史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為了將這些方法運用於無文字社會,鮑亞士主張田野研究者的任務,就是生產和蒐集無文字社會的文本。這個文本的型態,不僅是編譯當地語言的詞彙和語法,更是記錄關於社會關係和制度的神話、民間故事、信仰,甚至當地烹調風格的食譜。為了做到這一點,鮑亞士相當依賴與當地識字的民族誌研究者相合作(在夸扣特爾人中,最常合作的對象是喬治·亨特(George Hunt)),且他鼓勵學生們將這些人視為寶貴的夥伴,他們在西方社會的地位居於下等,但在理解他們自己文化時他們居於較高地位(見Bunzl 2004: 438-439)。
鮑亞士運用這些方法於1920年發表另一篇文章,其中他重新探討他對夸扣特爾人親屬關係的早期研究。在1890年代晚期,鮑亞士試圖藉由將夸扣特爾人的氏族組織,與它的南北相鄰社群的氏族組織相比較,以重建夸扣特爾氏族組織的轉變過程。但到了1920年,他反對將夸扣特爾人的親屬群體原則翻譯成任何一個英文詞彙。他並不是試圖將夸扣特爾人塞進某些更大的模型,而是試圖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理解他們的信念和行為。例如,儘管他先前將夸扣特爾人的單字「numaym」譯為「clan」(氏族),他在1920年轉而主張,最好將這個單字理解為一大筆特權,沒有任何英文單詞可用來表達這個意思。男人們透過他們的父母或妻子來保有主張這些特權的權利,而且可透過許多方式來獲得、運用這些特權,且代代相傳。正如在他對於交互語音的研究工作,鮑亞士終於認識到,對於夸扣特爾人親屬關係的各種不同的民族學解釋方式,是西方人概念範疇的侷限所造成的結果。正如他對於阿拉斯加人針箱的研究工作,他將各種夸扣特爾人行為的變異,視為社會形態與個體創造力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
科學家的社會運動家角色
- 我致力於兩件事情:絕對的學術與精神自由,以及將國家置於個人利益之下;換句話說,促進個人可發展其最佳能力的各種條件;只要這有可能對於傳統加諸於我們的枷鎖產生充分的理解;以及對抗國家或私人組織所施行的威權政策。這意味著投身於真正的民主原則。我反對意圖矇蔽心智的口號教條,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口號(鮑亞士致函杜威,1939年6月11日)。
在其他學科的許多社會科學家往往苦惱於他們「科學」工作的正當性,並不斷強調他們研究工作的超然、客觀與可計量等等性質的重要性。也許因為鮑亞士,如同其他早期人類學家,原先的訓練是自然科學,他與學生們從未表現出這種焦慮。更進一步,他並不相信超然、客觀與可計量等等性質,在使得人類學具有科學性方面是有其必要的。由於人類學家的研究目標有別於物理學家的目標,他推斷人類學家必須運用不同的方法與標準來評估他們的研究。因次,鮑亞士運用統計學研究,來呈現資料的變異程度是依據脈絡而定的,並主張人類變異性的這種依脈絡而定的本質,使得許多對於人種的科學理解所產生的抽象分析與概述(特別是當時的社會演化理論),事實上變得並不科學。他對於民族誌田野工作的理解,始於一項事實,民族誌研究的對象(例如巴芬島的因紐特人)不僅是客體,更是主體,而且他的研究讓他注意到他們的創造力與動力。更重要的是,他將因紐特人視為老師,因此翻轉了傳統上在科學家與研究客體之間的階層關係。
這項對於人類學家與他們所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所做的強調----重點在於,雖然天文學家研究星球;化學家研究元素;植物學家研究植物,但兩者基本上是不同的,然而人類學家與他們所研究的人,同樣都是人類—這意味著人類學家本身可能成為人類學研究的對象。雖然鮑亞士並未有系統地探求這個反方向的研究,他對於交互聲音的研究可以做為一個例子,說明他意識到科學家不應對他們的客觀性感到有信心,因為他們也是透過他們文化的稜鏡來看這個世界。
學生與影響力
從1901年到1911年,哥倫比亞大學只產生了七位人類學博士。儘管依據今日的標準,這是非常小的數目,在當時卻足以讓鮑亞士在哥大建立的人類學系,成為美國最卓越的人類學課程。此外,鮑亞士的許多學生繼續在其他主要大學建立人類學課程。
鮑亞士的首位博士生是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1901年),他連同鮑亞士的另一位學生羅伯特·羅維(1908年)創建了柏克萊加州大學的人類學系。他也培養了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1904年)——首批土著美國印第安人類學家之一(福克斯人(Fox)),在1909年於菲律賓研究時遭到殺害——以及亞伯特·劉易斯(Albert B. Lewis)(1907年)。鮑亞士也培養了其他許多對學院人類學的發展深具影響的學生:弗蘭克·斯佩克(1908年)由鮑亞士培養,卻在賓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迅速着手在該校創建人類學系;愛德華·薩丕爾(1909年)和費-庫珀·科爾(Fay-Cooper Cole)(1914年)在芝加哥大學發展了人類學系;亞歷山大·戈登衛塞(1910年)與埃爾西·克魯斯·帕森斯(她1899年從哥大獲得社會學博士,但後來向鮑亞士學習民族學)在社會研究新學院創立人類學系;萊斯利·斯皮爾(Leslie Spier)(1920年)後來在華盛頓大學和其妻子歐娜·甘瑟(也是鮑亞士的學生)創建人類學系,而梅爾維爾·赫斯科維茨(1923年)在西北大學創立人類學系。他也培養了約翰·里德·斯萬頓(在1900年取得哈佛博士之前,曾在哥大向鮑亞士學習兩年),保羅·拉丁 (1911年),露絲·潘乃德(1923年),格拉迪斯·理查德(Gladys Reichard)(1925年)於1921年在巴納德學院開始授課,後來升等為教授,露絲·班佐(Ruth Bunzel)(1929年),亞歷山大·萊瑟(Alexander Lesser)(1929),瑪格麗特·米德(1929),以及吉恩·韋爾特菲什(Gene Weltfish)(她在1929年論文答辯,儘管她直到1950年哥大降低所需費用後,才正式畢業)。
他在哥大的學生還包括墨西哥人類學家曼紐爾·加米歐,他在1909到1911年師從鮑亞士後獲得碩士學位,並於1917年成為墨西哥人類學局首任局長;以斯帖·戈德弗蘭克(Esther Goldfrank)於1919年隨鮑亞士前往新墨西哥州從事對普布羅印第安人的研究;吉爾伯特·弗雷耶,他在巴西形塑了「種族民主」的概念;以及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小說家卓拉·尼爾·赫斯特,她1928年從巴納德學院畢業——這是附屬於哥大的女子學院。
他也影響了克勞德·李維史陀(,後者是他在晚年寓居紐約時,於1940年代遇到的。
鮑亞士的幾位學生持續擔任美國人類學會的旗艦期刊《美國人類學家》的編輯:約翰·里德·斯萬頓(1911, 1921-1923),羅伯特·羅維(1924-1933),萊斯利·斯皮爾((1934-1938),以及赫斯科維茨 (1950-1952)。愛德華·薩丕爾的學生John Alden Mason在1945-1949年當編輯,而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和羅伯特·羅維的學生沃爾特·戈德施米特(Walter Goldschmidt)在1956-1959年擔任編輯。
鮑亞士的大多數學生同樣具有他對謹慎的歷史重建的關注,以及他對臆測的演化模型的反感。此外,鮑亞士鼓勵他的學生,批評他們自己就如同其他人批評他們一樣。例如,鮑亞士起初為他將頭骨指數(頭骨形態的有系統變異)做為描述遺傳特徵的方法提出辯護,但後來在進一步研究後否定了他早期的研究;他同樣批評了他自己對(太平洋西北海岸)瓜求圖人語言及神話的早期作品。
鮑亞士的學生受到此種自我批判動力所鼓舞,以及鮑亞士學派致力於從報導人那裡學習,並根據個人的研究發現來塑造論點,因此這些學生迅速偏離了他自己的研究論點。他的學生很快試圖發展鮑亞士普遍反對的鉅型理論。克魯伯使他同事的注意力轉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分析二者結合的可能。露絲·潘乃德發展了「文化與人格」以及「國民文化」(national cultures)理論,而克魯伯的學生朱利安·斯圖爾德發展了文化生態學及多線演化論。
然而,鮑亞士對於人類學具有不朽的影響。事實上所有人類學家如今都接受鮑亞士對經驗論及他的方法論文化相對論的支持。此外,事實上所有文化人類學家如今都分享着鮑亞士對田野研究的貢獻,這包括長期居住,學習當地語言,並與報導人發展社會聯繫。最後,人類學家繼續尊崇他對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Thomas Gossett在1963年《種族:在美國的一個思想的歷史》(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一書中,寫道:「在歷史上,鮑亞士在打擊種族主義偏見上,可能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
引用文獻
- ↑ http://www.franz-boas.com -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Boas´ birth at Minden e. g. an exposition, a scientific meeting, a theatre play, a special medal, an edition of the diary of Wilhelm Weike, Boas´ servant on Baffin Island
- ↑ Norman F. Boas, 2004, p. 291 (photo of the graveyard marker of Franz and Marie Boas, Dale Cemetery, Ossining, N.Y.)
- ↑ Holloway, M. (1997) The Paradoxical Legacy of Franz Boas - father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Natural History. November 1997
- ↑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339265/346507
- ↑ Franz Boas
- ↑ Douglas Cole 1999 Franz Boas: The Early Years, 1858-1906 p. 280. Washington: Douglas and MacIntyre.
- ↑ Franz Boas' letter-diary to Marie Krakowizer,1883年11月23日 Baffin Island Letter-Diary, 1883-1884, edited by Herbert Cole (1983:33)
- ↑ Alexander Lesser, 1981 "Franz Boas" p. 25 in Sydel Silverman, ed. From Totems to Teachers New Yort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A reassessment of human cranial plasticity: Boas revisited by Corey S. Sparks and Richard L. Jantz.
- ↑ Marks, Jonathan What it Means to be 98% Chimpanzee: Apes, People, and Their Gen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ISBN 0-520-24064-2 p. xviii C. Gravlee、H. Russell Bernard與William R. Leonard重新分析鮑亞士的資料,並論定鮑亞士當初的發現大致正確。此外,他們將新的統計方法、電腦輔助研究法運用於鮑亞士的資料,並發現更多支持頭骨可塑性觀點的證據<ref>New Answers to Old Questions: Did Boas Get It Right? Heredity, Environment, and Cranial Form: A Reanalysis of Boas’s Immigrant Data .
- ↑ Did Boas Get It Right or Wrong?
資源/延伸閱讀
鮑氏著作
- Boas n.d. "The relation of Darwin to anthropology," notes for a lecture; Boas papers (B/B61.5)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Published on line with Herbert Lewis 2001b.
- Boas, Franz 1911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ISBN 0-313-24004-3
- Boas, Franz 1912 Changes in the Bodily Form of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4, No. 3, July-Sept, 1912.
- Boas, Franz 1912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ac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XXI, pp. 177–183.
- Boas, Franz 1922 Report on an Anthropometric Investiga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une 1922.
- Boas, Franz 1922 The Measuremen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able Quantities. 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December, 1922.
- Boas, Franz 1927 The Eruption of Deciduous Teeth Among Hebrew Infants. The Journal of Dental Research, Vol. vii, No. 3, September, 1927.
- Boas, Franz 1935 The Tempo of Growth of Fratern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21, No. 7, pp. 413–418, July, 1935.
- Boas, Franz 1940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ISBN 0-226-06241-4
- Stocking, George W., Jr., ed. 1974 A Franz Boas Reader: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83-1911 ISBN 0-226-06243-0
- Boas, Franz 1928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2004 ed.) ISBN 0-7658-0535-9
受鮑氏影響著作與鮑氏人類學
- Bashkow, Ira 2004 "A Neo-Boasian Conception of Cultural Boundarie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6(3): 443-458
- Bunzl, Matti 2004 "Boas, Foucault, and the 'Native Anthropologist,'"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6(3): 435-442
- Cole, Douglas 1999 Franz Boas: The Early Years, 1858-1906 ISBN 1-55054-746-1
- Kuper, Adam 1988 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 Transformations of an Illusion ISBN 0-415-00903-0
- Kroeber, Alfred 1949 "An Authoritarian Panacea"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1(2) 318-320
- Lesser, Alexander 1981 "Franz Boas" in Sydel Silverman, ed. Totems and Teachers: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ISBN 0-231-05087-9
- Lewis, Herbert 2001a "The Passion of Franz Boa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3(2): 447-467
- Lewis, Herbert 2001b "Boas, Darwin,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42(3): 381-406 (On line version contains transcription of Boas's 1909 lecture on Darwin.)
- Stocking, George W., Jr. 1968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ISBN 0-226-77494-5
- Stocking, George W., Jr., ed. 1996 Volksgeist as Method and Ethic: Essays on Boasian Ethnography and the Germ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ISBN 0-299-14554-9
鮑亞士、人類學及其猶太認同
- Glick, Leonard B. 1982 "Types Distinct from Our Own: Franz Boas on Jewish Identity and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4(3) pp. 545–565.
- Frank, Gelya 1997 "Jews, Multiculturalism, and Boasian Anthropology"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9(4), pp. 731–745.
- Mitchell Hart 2003 "Franz Boas as German, American, Jew." In German-Jewish Identities in America, eds. C. Mauch and J. Salomon (Madison: Max Kade Institute), pp. 88–105.
- Kevin MacDonald 1998 The Culture of Critique: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Jewish Involve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chapter 2 provides a critique of Boas, by resurrecting the Nazi notion of "Jewish science".
外部連結
- A reassessment of human cranial plasticity: Boas revisited—Summary of critical paper by Corey S. Sparks and Richard L. Jantz.
- Heredity, Environment, and Cranial Form—article confirming Boas's research, by Clarence C. Gravlee, H. Russell Bernard, and William R. Leonard
- Franz Boas Out of the Ivory Tower—essa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ademy and politics, drawing on the example of Boas
- The Great Social Anthropology Scam, Chris Brand — article from The Occidental Quarterly, a website and journal advocating white nationalist opinions, examining what the author describes as the "destructive legacy of Franz Boas".